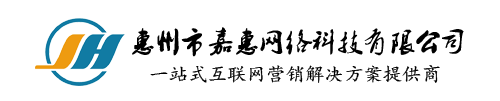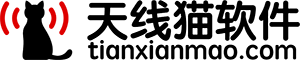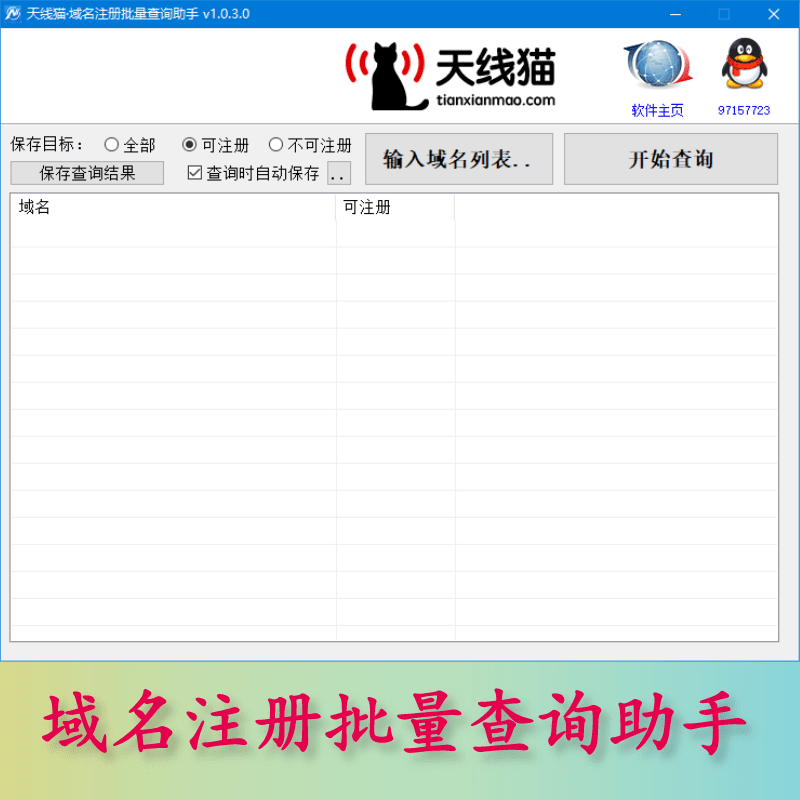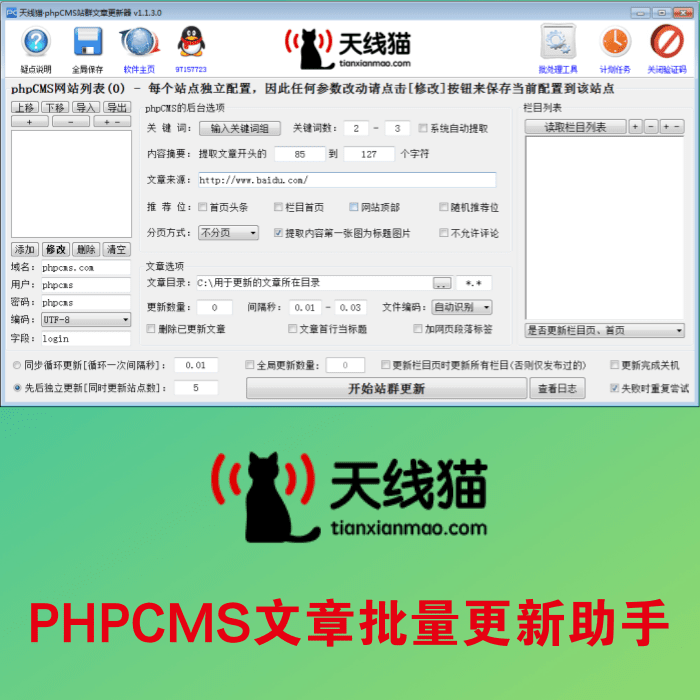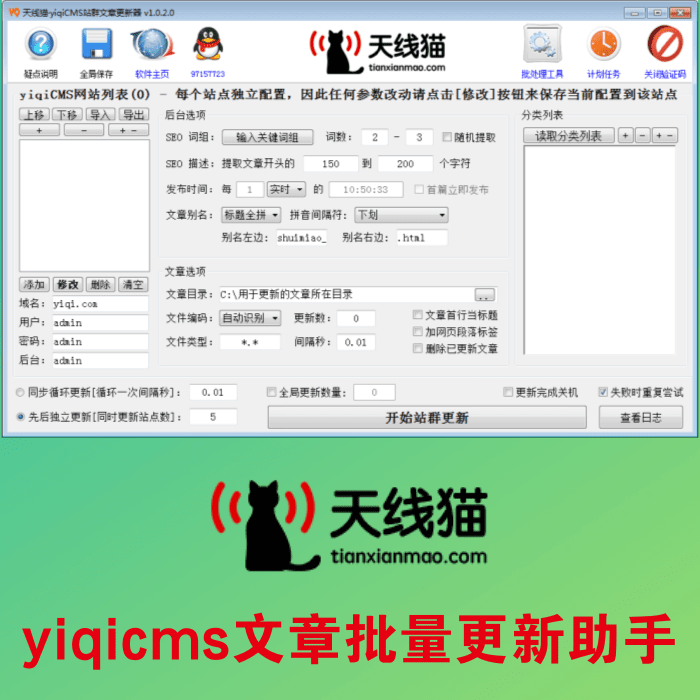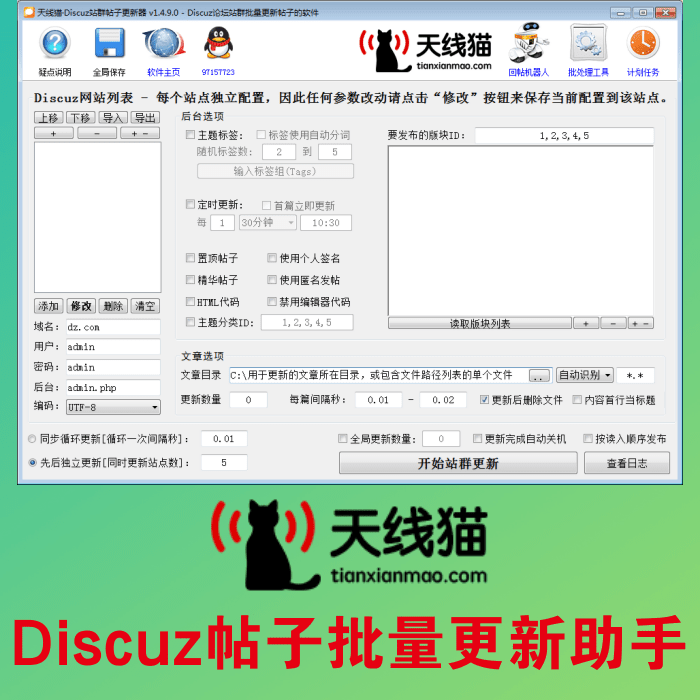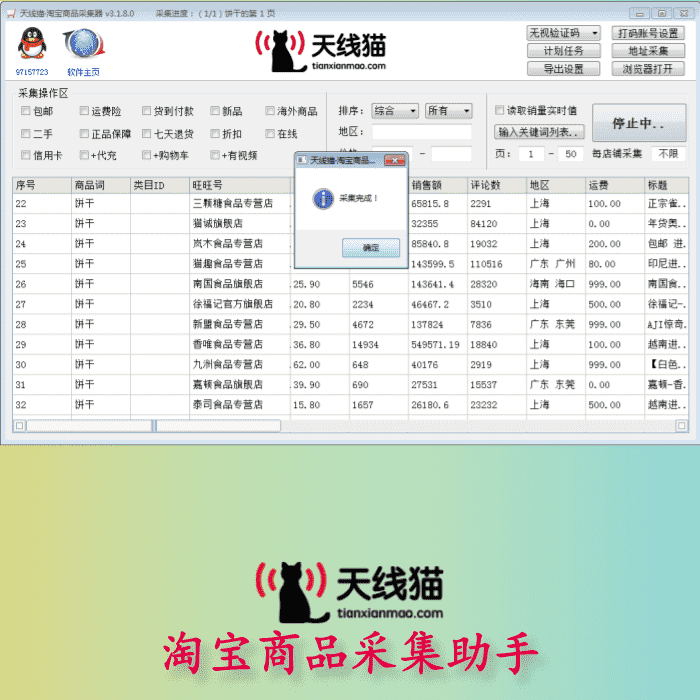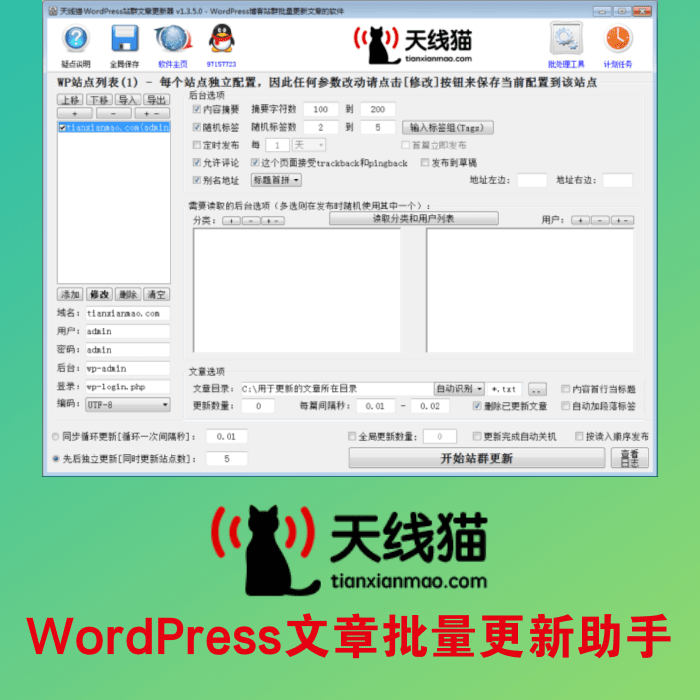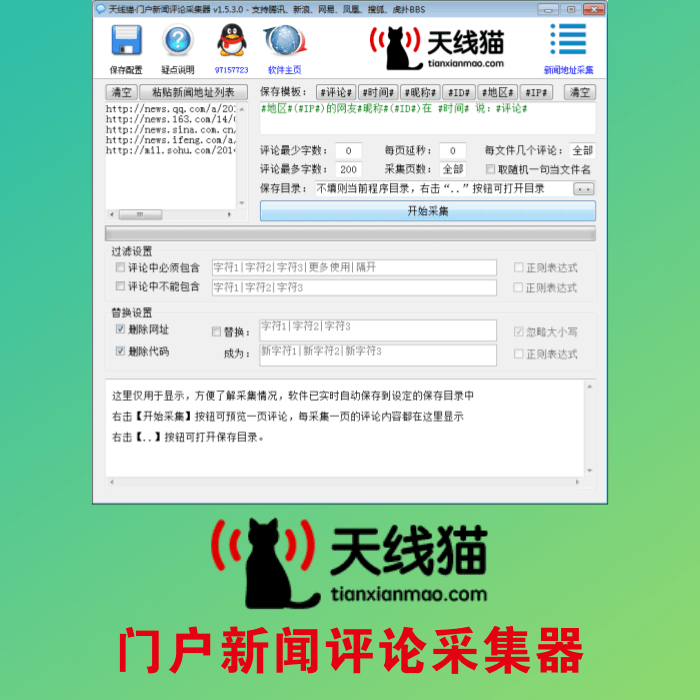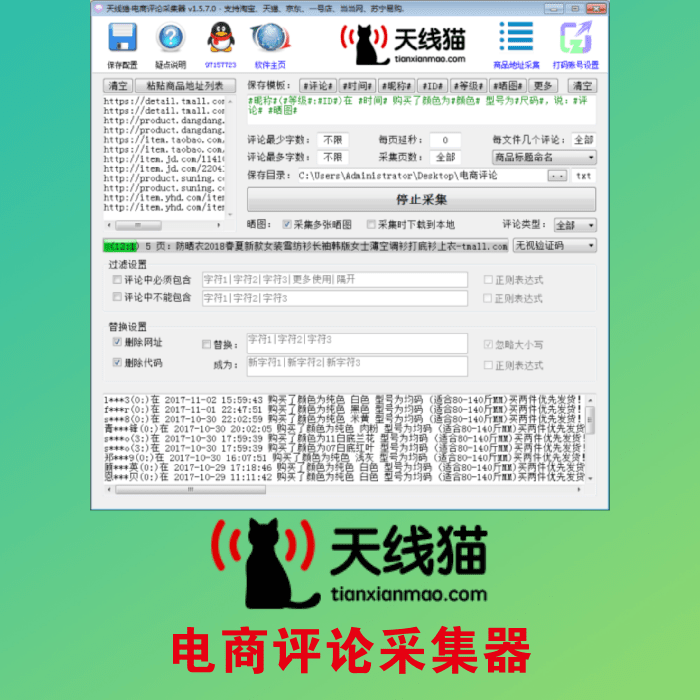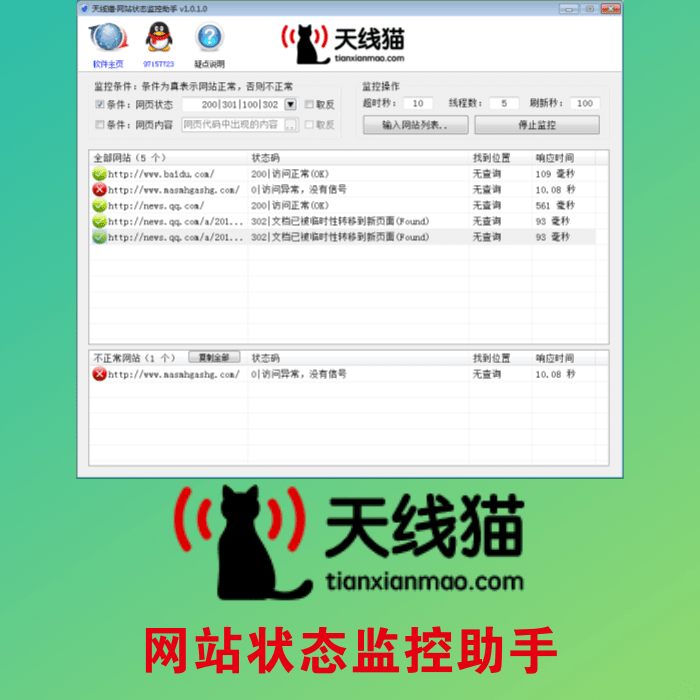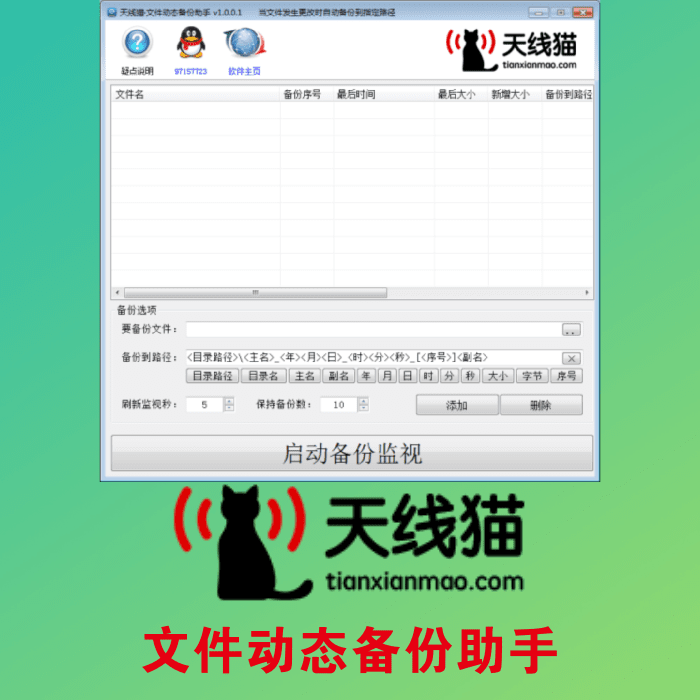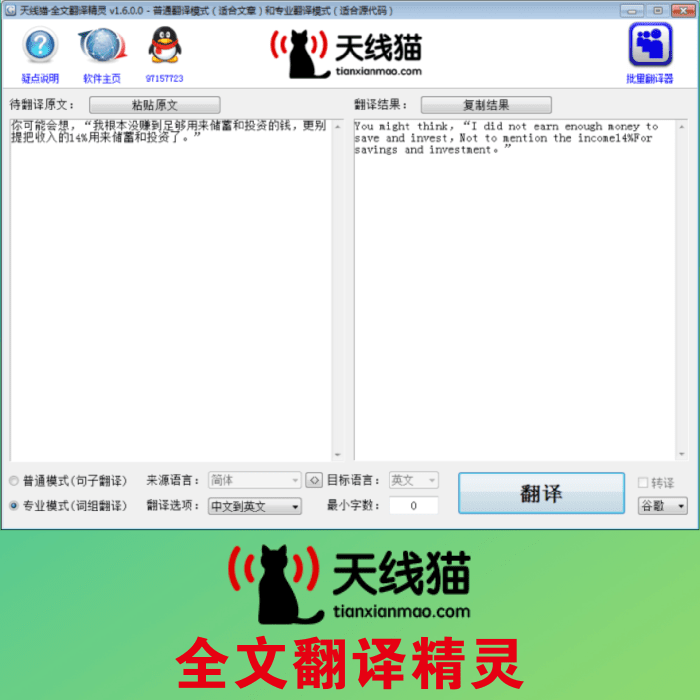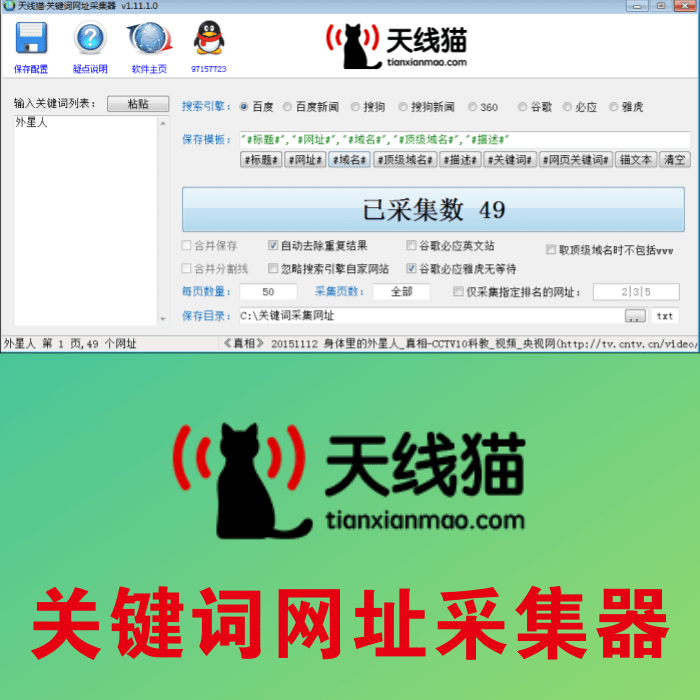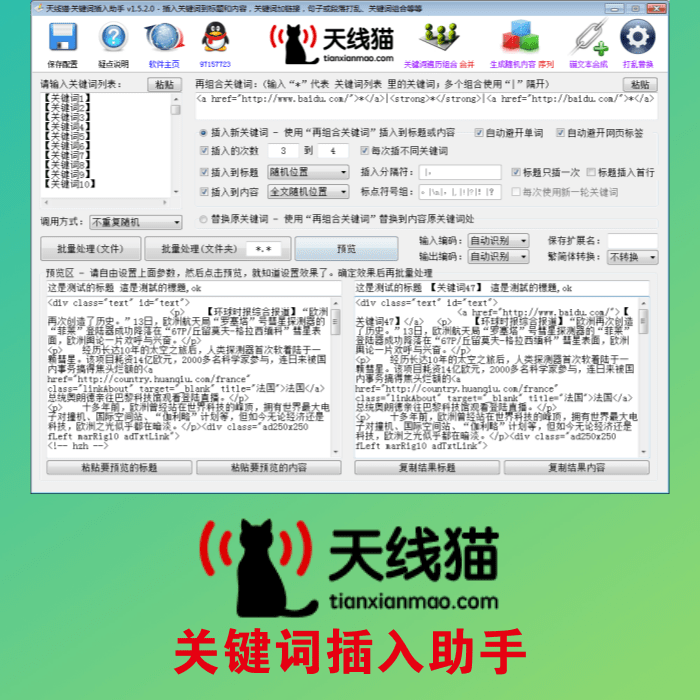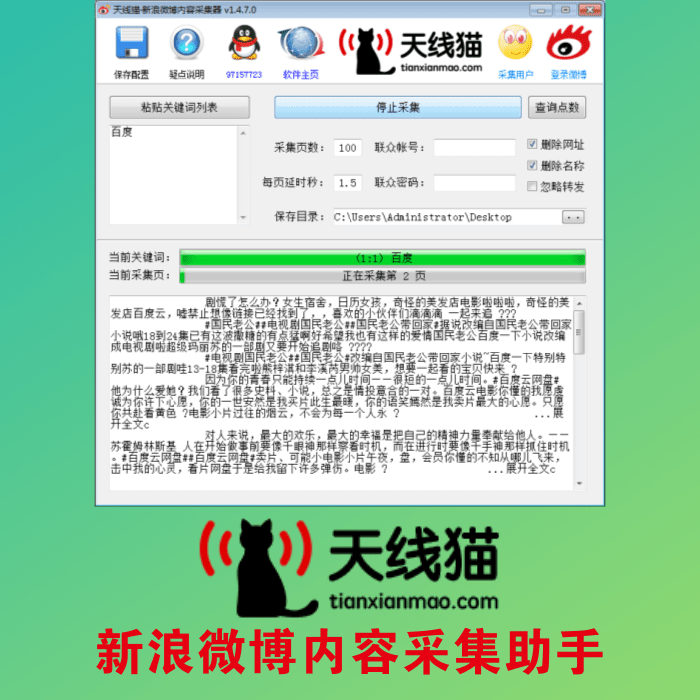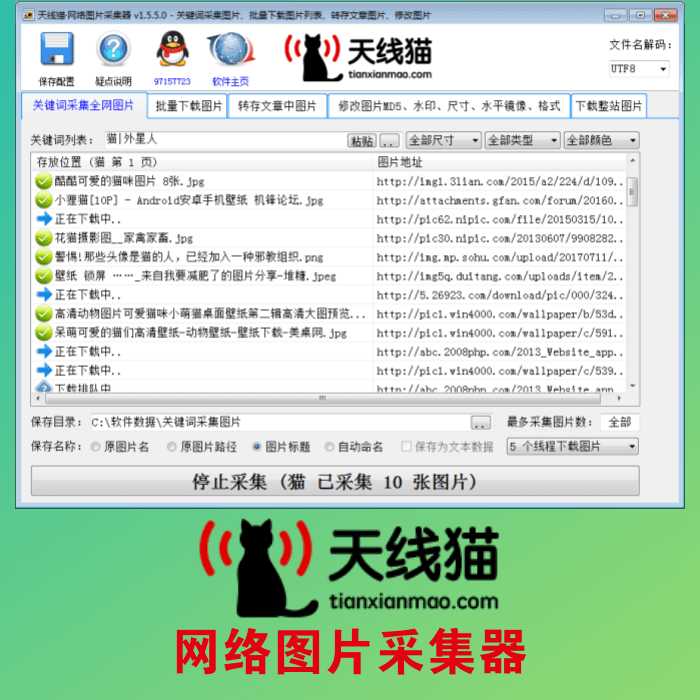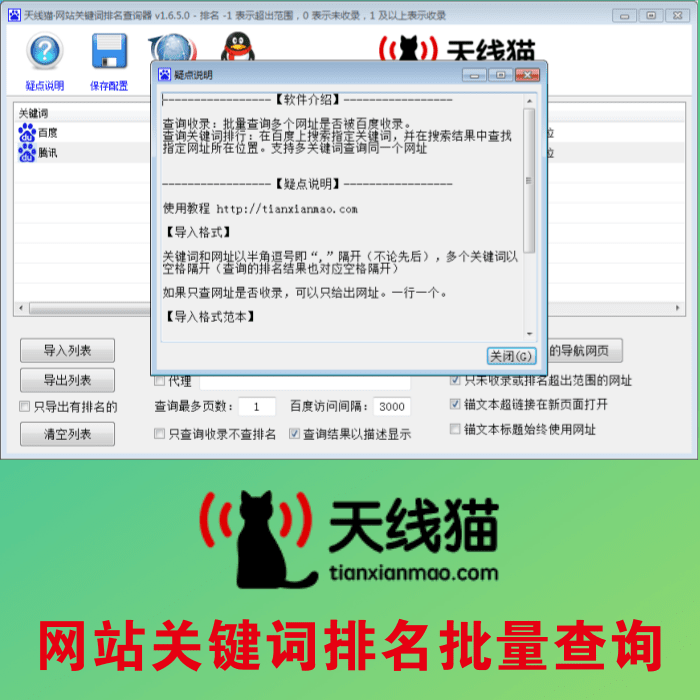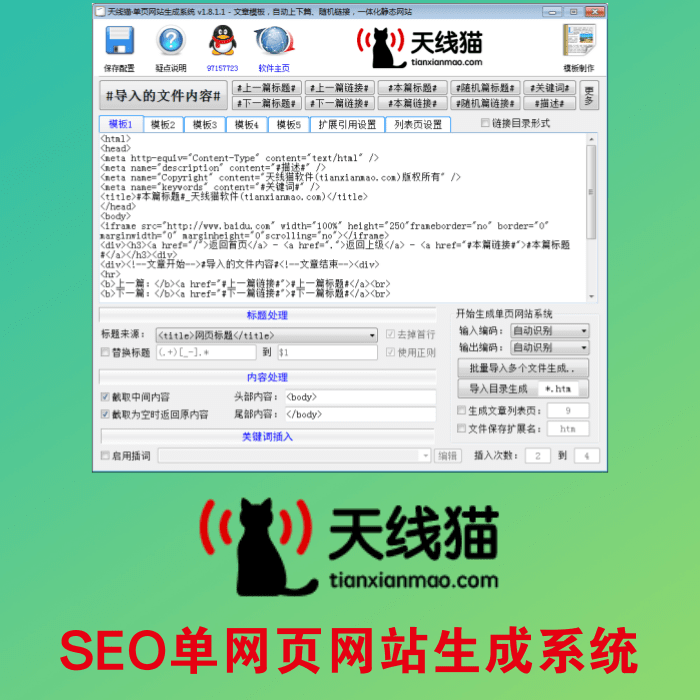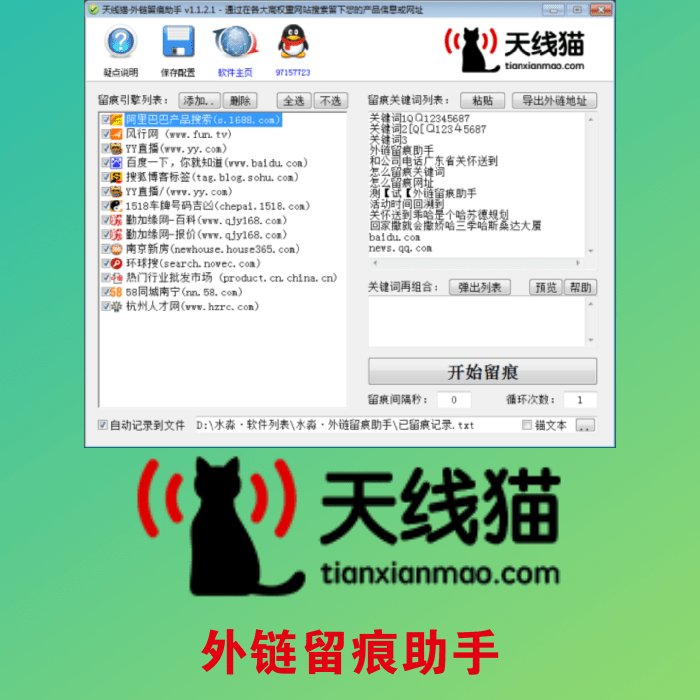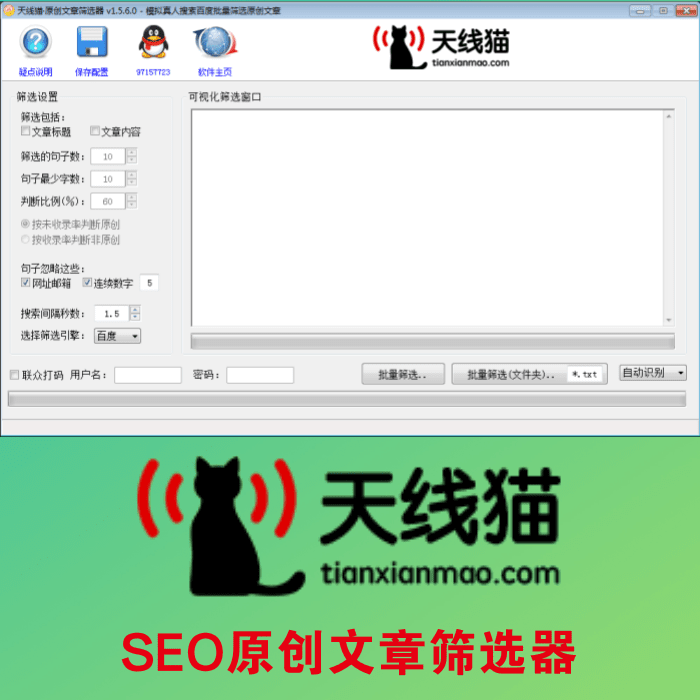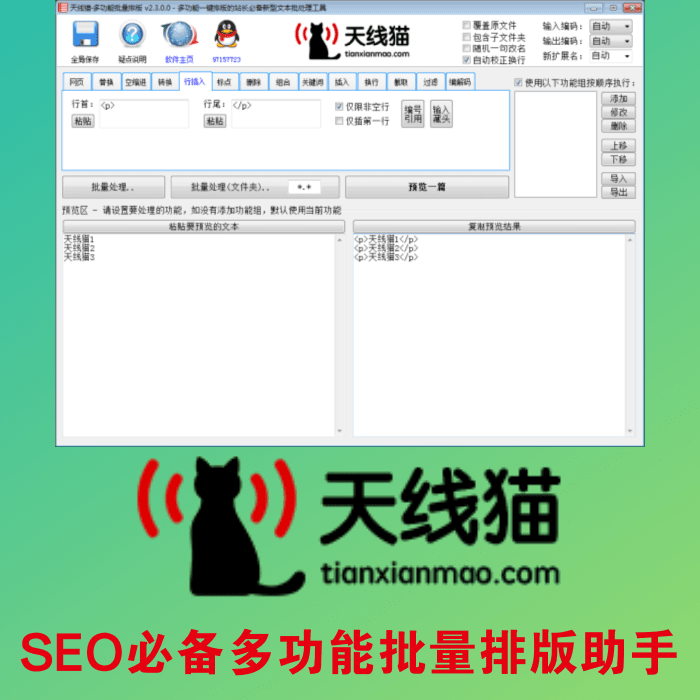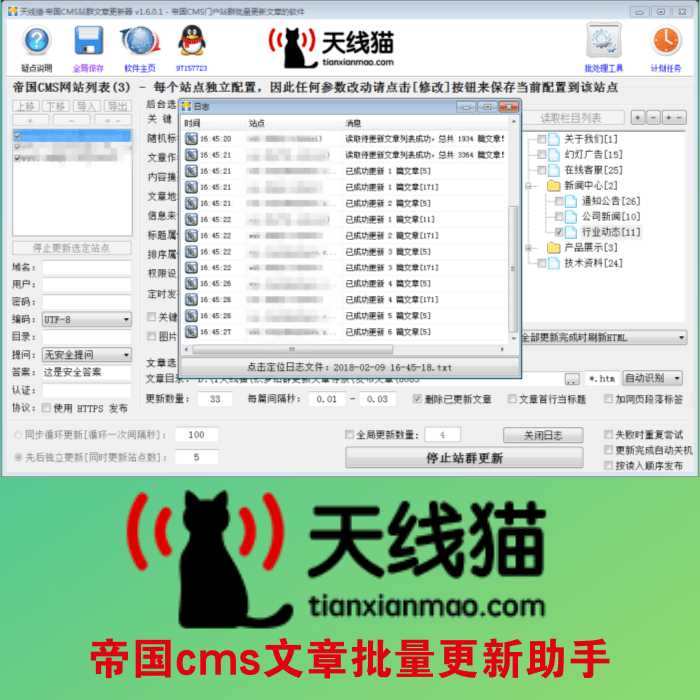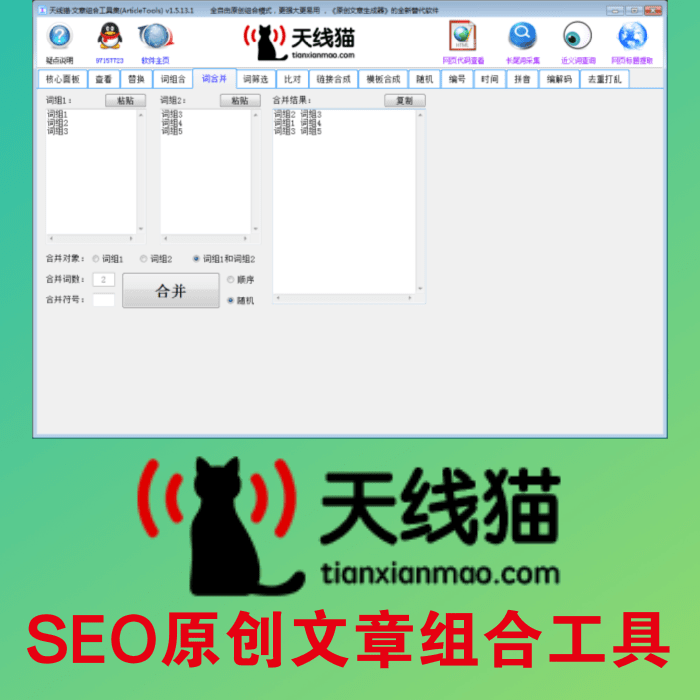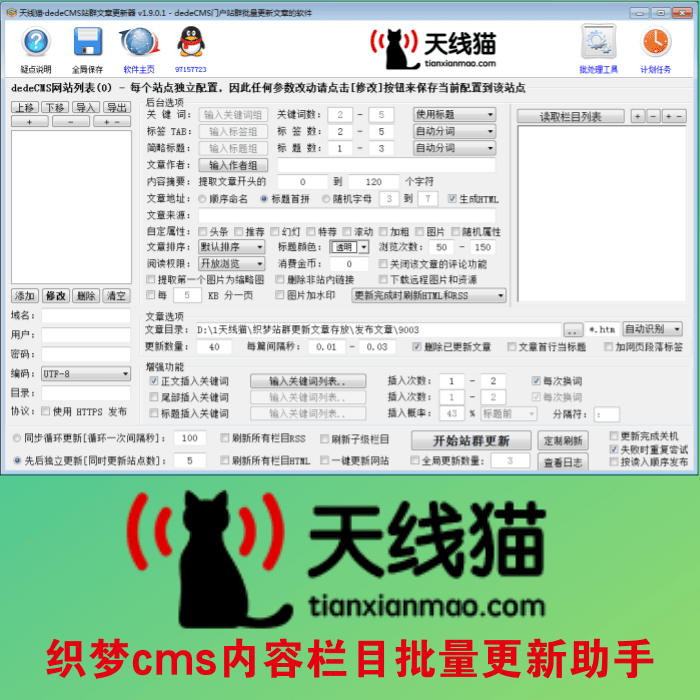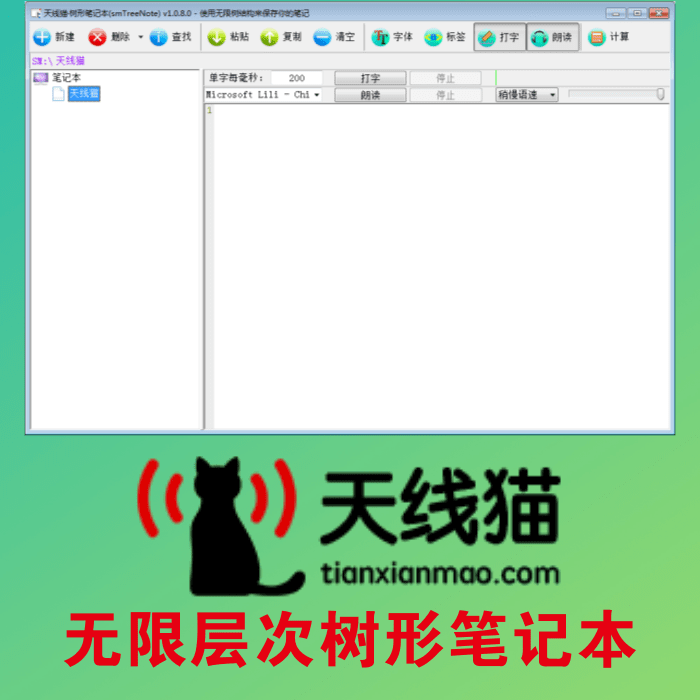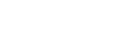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起草《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下稱《指南》),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根據指南對“平臺經濟”的解釋,只要跟線上經濟有關的互聯網平臺都將在監管范圍之內。 終于,從螞蟻到大型互聯網公司,到整個互聯網平臺行業,都進入了監管范圍。
這是中國首次嘗試界定科技行業的反競爭行為,也將從根本上改變互聯網公司在中國的競爭版圖。相較于歐洲的十年反壟斷,中國反壟斷,雖遲必到。進行控制和加強監管的背后,是每個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數字經濟綜合發展的聰明考量。
《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一經發布,聚集國內主要互聯網巨頭的港股市場應聲暴跌。
恒生科技指數一度跌超6%,阿里、京東、騰訊、美團等集體低開低走。截至11月10日港股收盤,美團-W股價大跌超10%,京東-SW跌近9%,阿里跌超5%,騰訊跌超4%。4家巨頭一天合計蒸發市值超過8800億港元。
此次反壟斷新規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震蕩和影響,是因為這是中國國家市場監督治理總局首次直接打擊互聯網行業的反競爭行為,也是中國監管部門邁出遏制國內科技巨擘壟斷力量的第一步。

文件稱,此次《指南》的制定旨在預防和制止互聯網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具體內容來看,反壟斷指南對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等四個方面的壟斷現象做出了界定。
其中,“算法”“數據”“技術”“成本”被頻繁提詞,而這些正是互聯網巨頭在進入某個藍海領域初期繞不開的要害詞。一旦形成壟斷,這也將成為抵制競爭與創新的利益工具。
在經營者集中部分,指南提到了協議控制(VIE)架構:涉及(VIE)架構的經營者集中,屬于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范圍。達到國務院規定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
事實上,監管機構采取此舉的同時,中國的各大互聯網巨頭已經控制了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中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一直在打造日益霸道的生態系統。比如,使用微信支付的用戶不能在阿里巴巴的淘寶網上商店購物,也不能在微信內輕松共享淘寶商品的鏈接。
此外,“二選一”和“大數據殺熟”現象層出不窮。“二選一”從來都不是一個新現象,中國的電商行業長期以其咄咄逼人的策略聞名。比如,一些在線賣家表示,阿里巴巴不公平地強迫他們僅在其平臺上進行銷售;從去年的格蘭仕起訴天貓,到今年唯品會與愛庫存的爭執。時下,“二選一”可以說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對于“大數據殺熟”來說,根據北京市消費者協會 2021 年 3 月發布的“大數據殺熟”問題調查結果,88.32% 被調查者認為“大數據殺熟”現象普遍或很普遍,且 56.92% 被調查者表示有過被“大數據殺熟”的經歷。
就在今年 9 月 15 日,央視財經頻道再次揭露大數據殺熟現象,指出在線旅游平臺針對不同消費特征的旅游者對同一產品或服務在相同條件下設置差異化的價格。
在《指南》中,不論是令用戶苦惱的“二選一”,還是大數據“殺熟”,抑或捆綁交易,低價傾銷以及拒絕交易等現象都被定義為壟斷。顯然,從很直接的理解看,此次《指南》直指這些互聯網平臺目前存在的問題,表明了當局的態度,是對指南里所指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進行規范監管的大綱。
另一方面,遏制巨頭發展似乎并不是新規的很終目的,反而是互聯網平臺的壯大對帶動中國經濟更高效發展功不可沒。事實上,除了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公平和秩序外,《指南》發布背后的用意更應得到重視。
反壟斷是一個嚴謹的法律問題,內容繁雜。但從其初衷來看,無非是全面而靈活地維護各方的合法利益。但是,在一個利益為目的的商業戰場上,要去維護各方的合法利益,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從各大互聯網平臺是否傷害消費者利益的考量來看,隨著市場的發展,人們對高科技公司的壟斷地位愈發感到不安。這些公司往往起源于單一市場,但是利用其技術,數據和基礎架構優勢逐漸發展為跨市場的綜合體,形成了所謂的生態圈。當人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幾家公司包圍,在享受了便利性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選擇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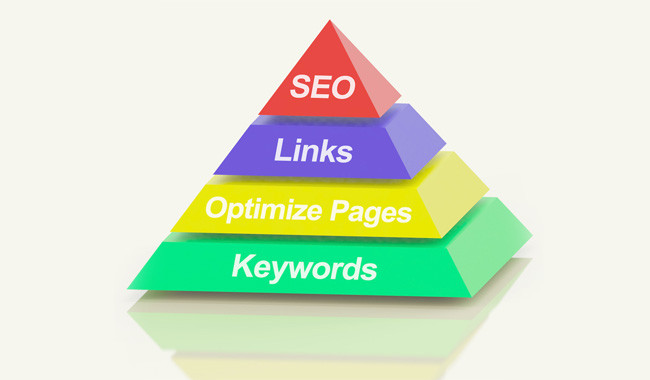
10月,美國司法部就指控谷歌利用與分銷商(包括web瀏覽器、智能手機制造商和移動通信運營商)的非法協議,確保其搜索引擎是擺在消費者面前的默認引擎。他們稱,“人們之所以使用谷歌,是因為他們選擇這么做——不是因為他們被迫這么做,也不是因為他們找不到替代品”。
于是,在市場份額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家平臺型企業的情況下,平臺會擁有對雙邊用戶的定價權、話語權以及規則制定權,贏者通吃。雖然用戶使用平臺的總成本會提高,比如蘋果公司對App內購采取30%抽成的“蘋果稅”,但潛移默化中使用習慣的建立以及較高的遷移成本會將用戶綁定,使得用戶和產品服務的提供商不得不共同承擔新增的使用成本。
平臺型企業同時會大力投入生態系統的建設,通過更多的產品與服務將更多類型的參與者納入到平臺的生態中,將雙邊的連接升級為多邊交互。成熟的生態系統一旦形成,這種多邊關系便具有很高的穩定性甚至有自我生長的能力,對系統中的參與者粘性較強而很難被顛覆。其中,平臺作為規則的制定者自然而然得處于生態的頂端,并且擁有很大的價值杠桿。
而從一整個互聯網平臺的長遠發展來看,享受壟斷紅利的平臺型企業往往也會極力壓制行業中潛在競爭對手生態的形成,利用現有的規則或資本端的收購去維護自身的地位,從而從另一層意義上偏離平臺自身以開放、互聯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初衷,反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整體福利。
這也是此次《指南》所指的核心所在——當多行業平臺型經濟走向主導的大趨勢,平臺與小企業之間的話語權不對等。參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力不對等,將長遠地損傷和影響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整體福利。
蘋果公司曾連續數次引用App Store的規則阻止Facebook Gaming在iOS端的上架。這主要因為FacebookGaming中存在游戲分發的功能,使得游戲開發商可以繞過蘋果的30%抽成,直接觸達終端消費者。直到Facebook將其中游戲庫頁面去掉后,這一App才成功過審,登陸App Store。
顯然,已然形成壟斷格局的行業中,挑戰者幾乎不可能在壟斷方制定的規則下與其正面競爭,往往只能通過合縱連橫團結上下游友商,等待技術性顛覆的洗牌機遇,嘗試另起爐灶。
此外,當平臺型企業形成壟斷格局后,還可能壓抑創新。平臺的核心作用是降低信息不對稱,以此來服務社會經濟運行,提升效率。而通過壟斷來扭曲信息、加劇信息不對稱則是其本意的對立面。當平臺型企業形成壟斷之后,其往往會盡力維持壟斷。在這一過程中,難免存在操縱價格、價格歧視、聯手抵制、非法兼并等不當競爭手法,很終壓抑了創新和競爭。
過去二十年里,“中國制造”實現了對全球范圍的覆蓋,而之后中國的企業也伴隨著“一帶一路”等戰略走向海外。那在產品出海、企業出海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平臺的出海。顯然,中國的平臺經濟有需要,且有能力向海外進行輻射,但一定是在各方利益的平衡下綜合發展。既不左支右絀,也不顧此失彼。
文章地址:http://www.brucezhang.com/article/online/6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