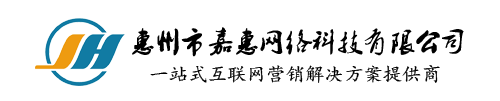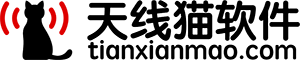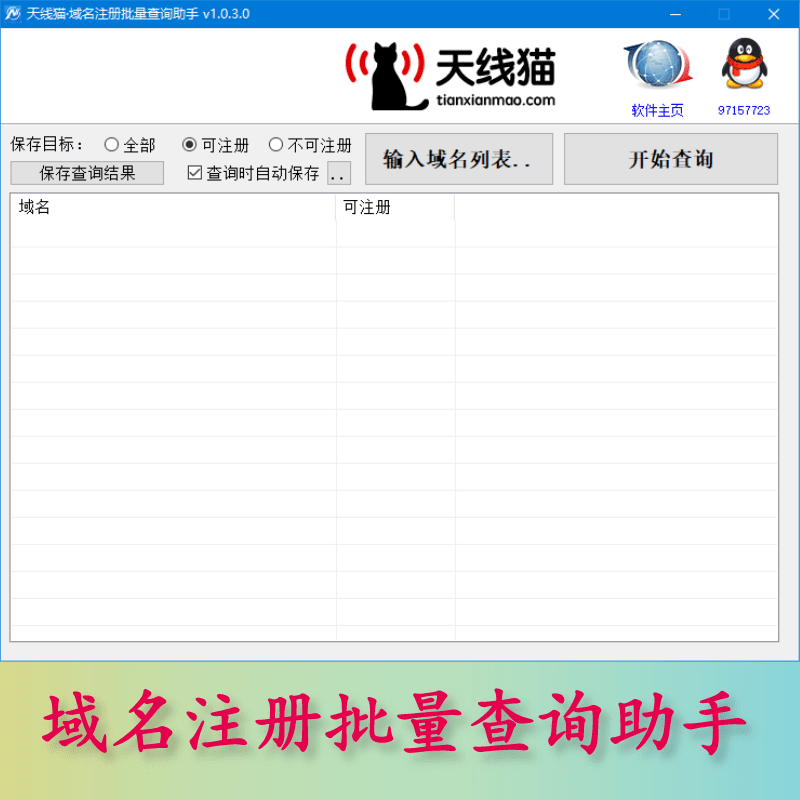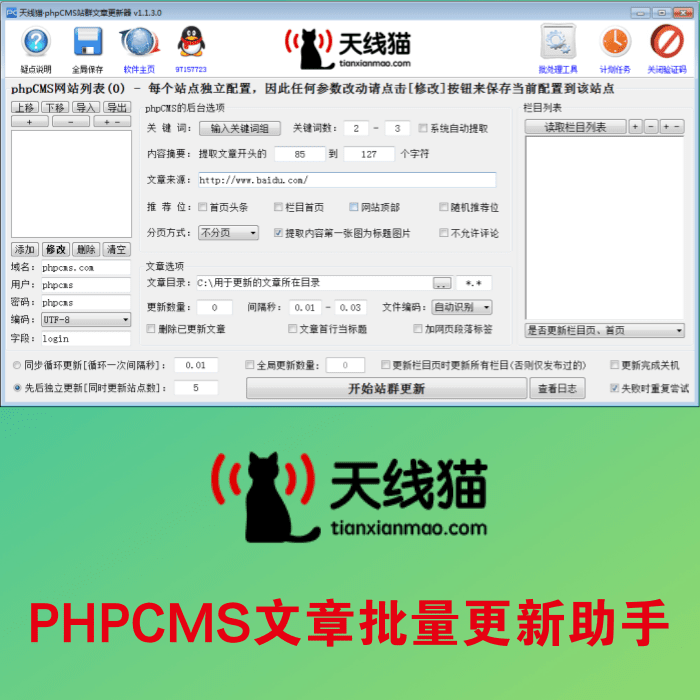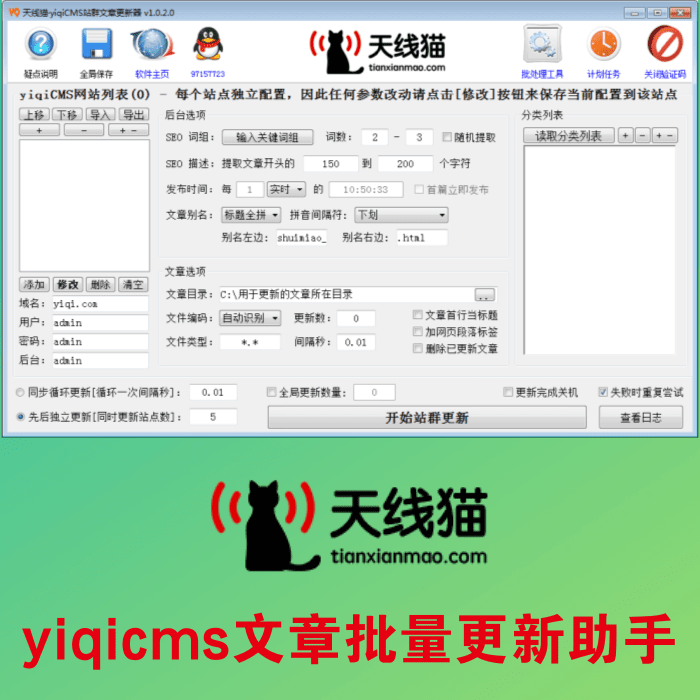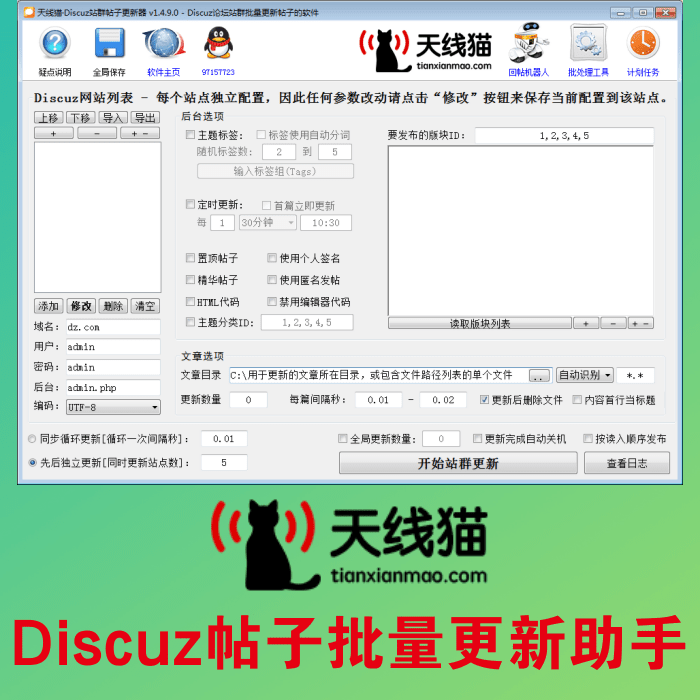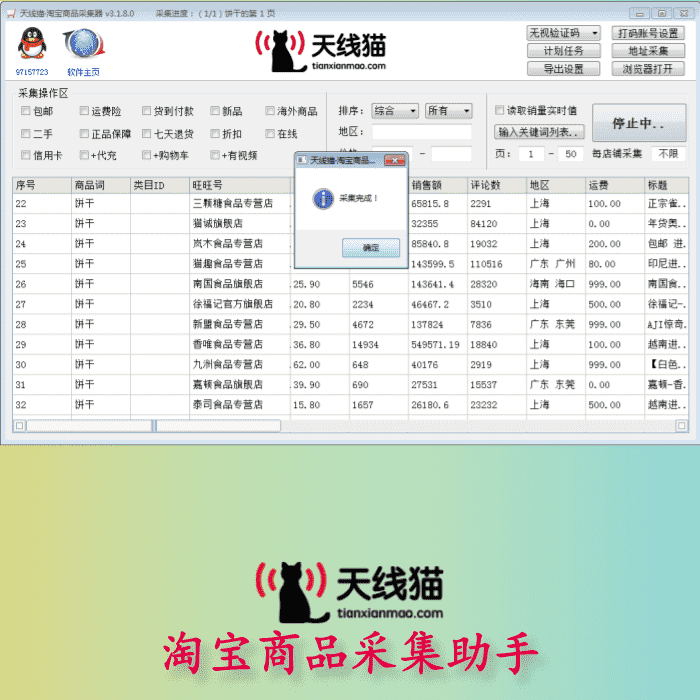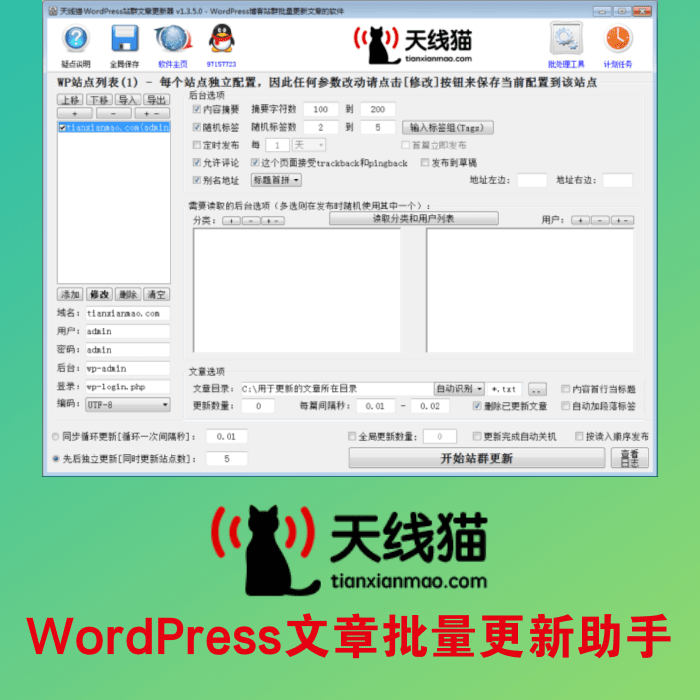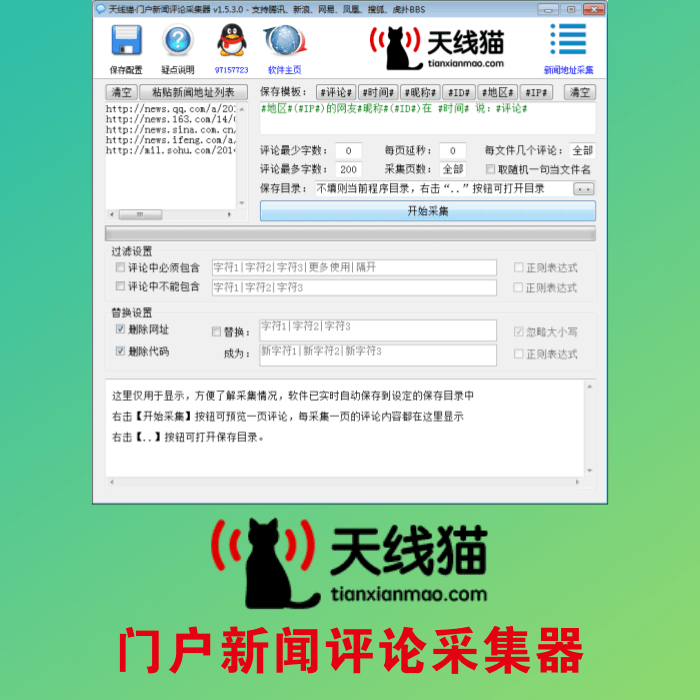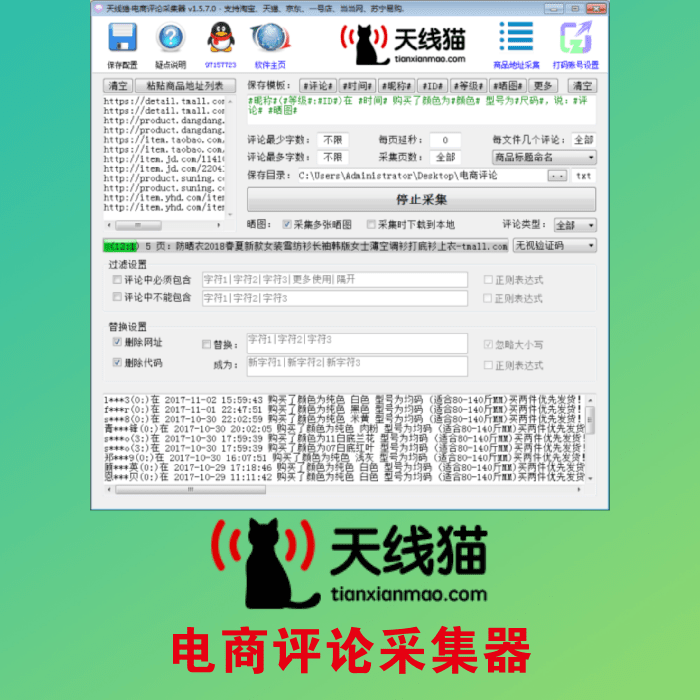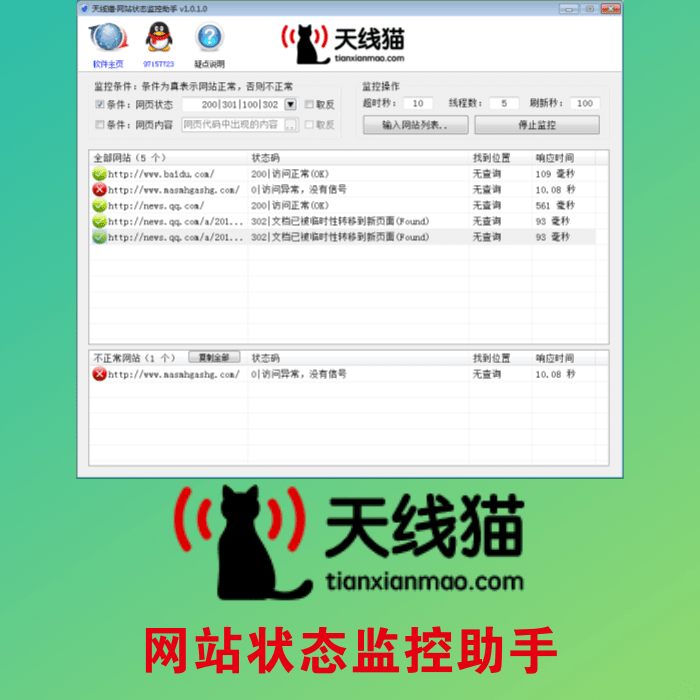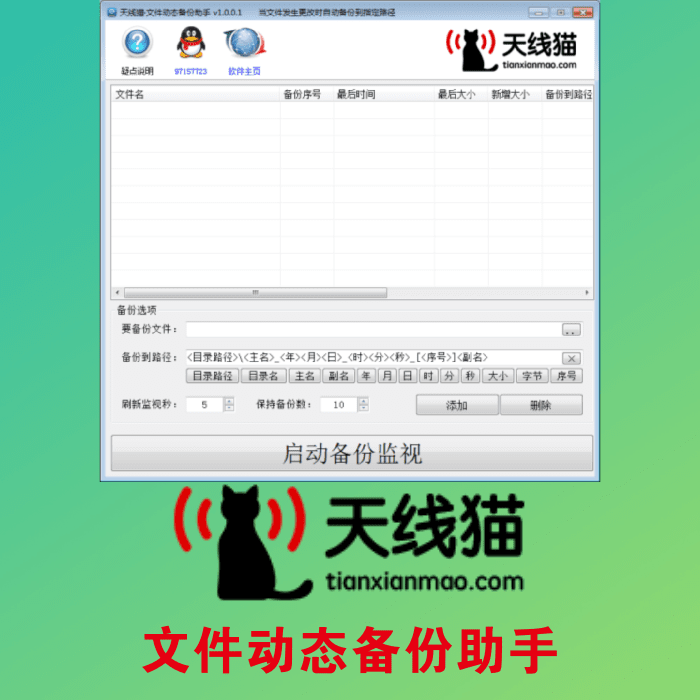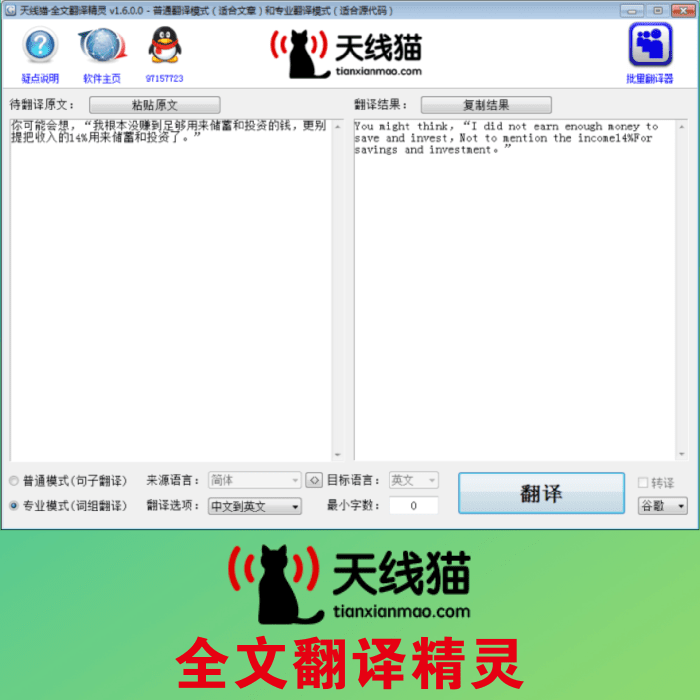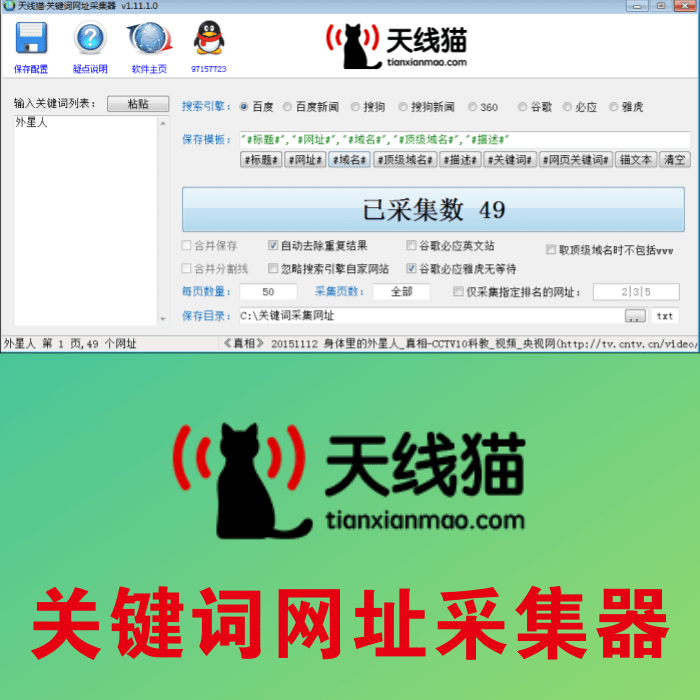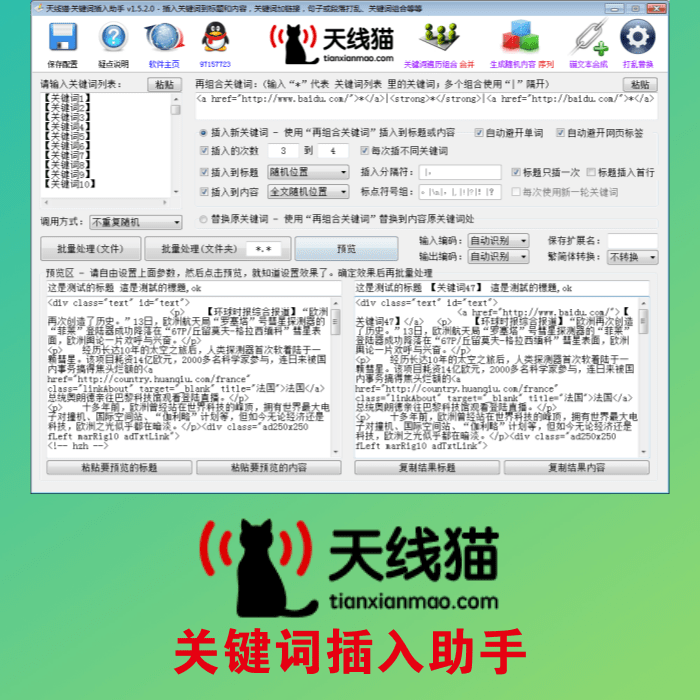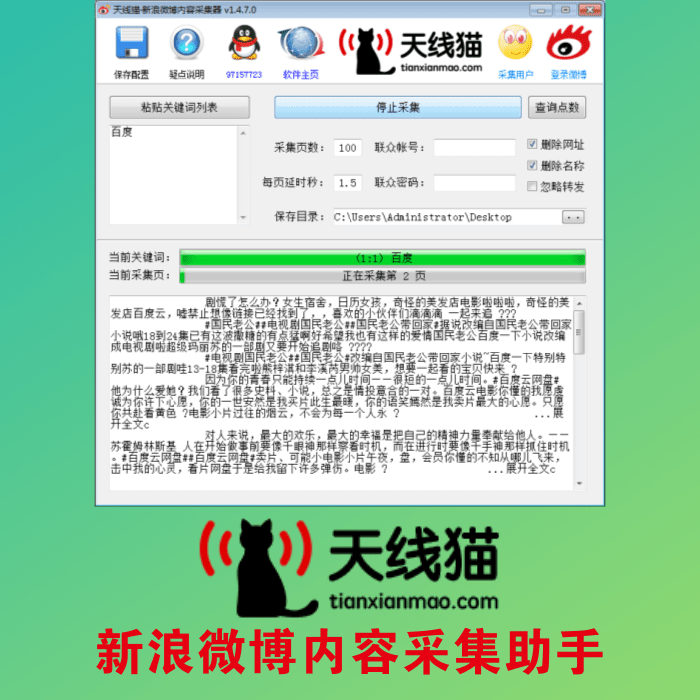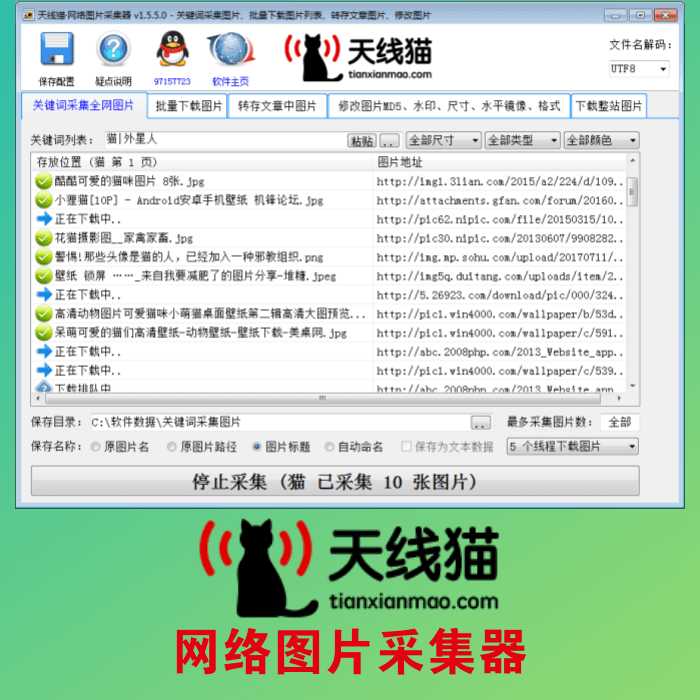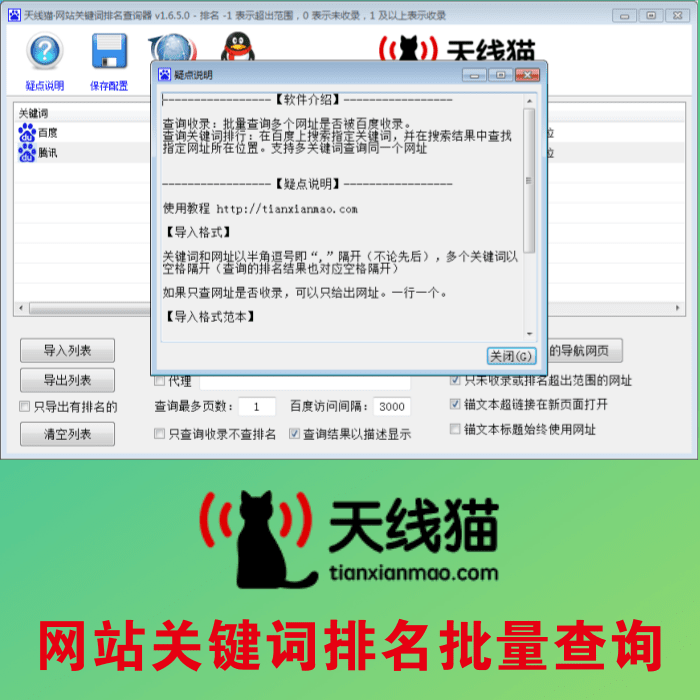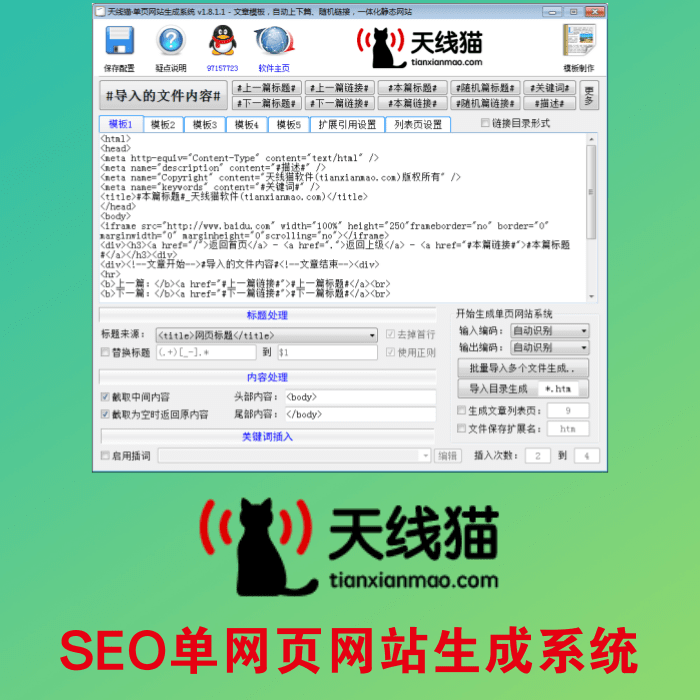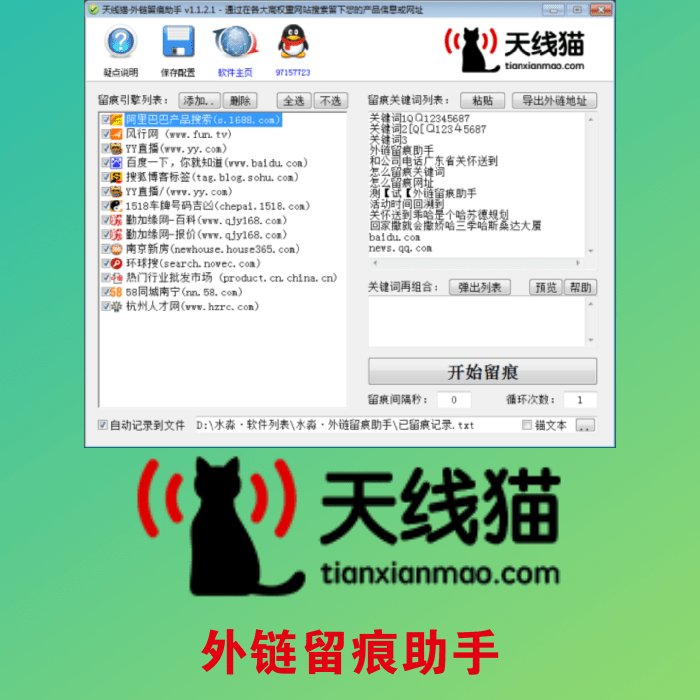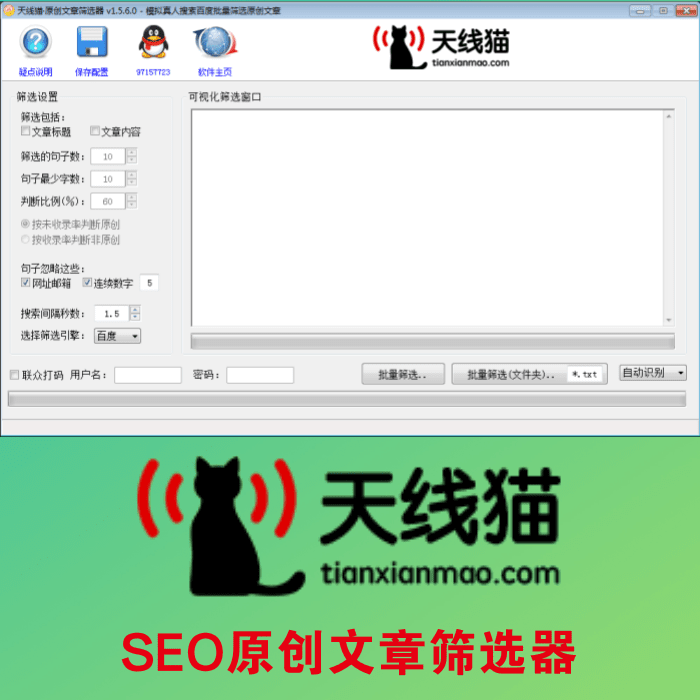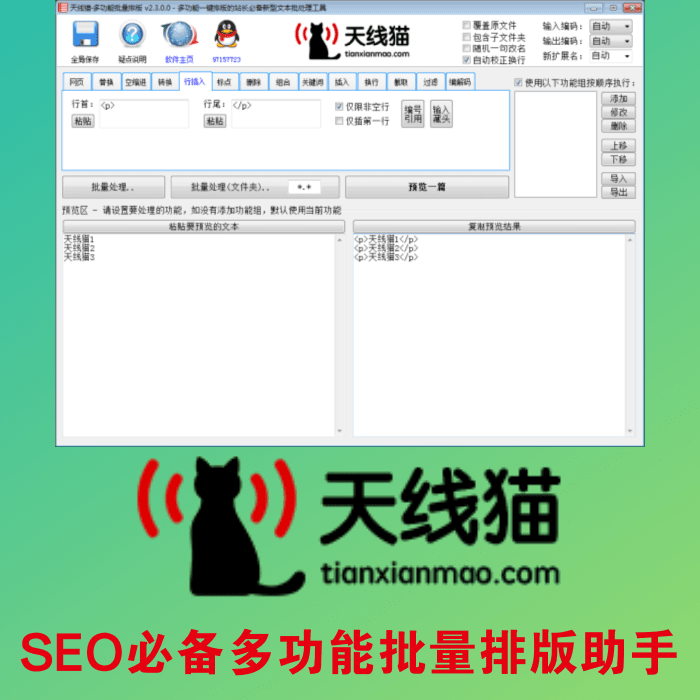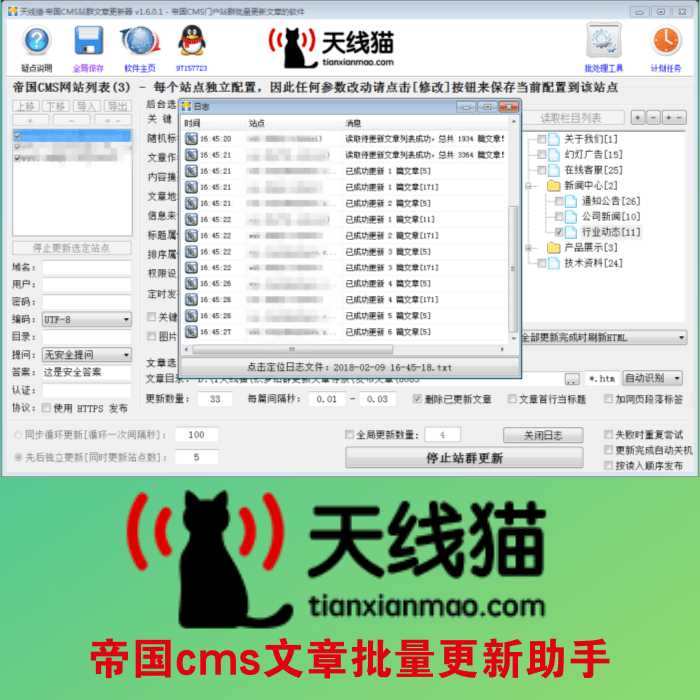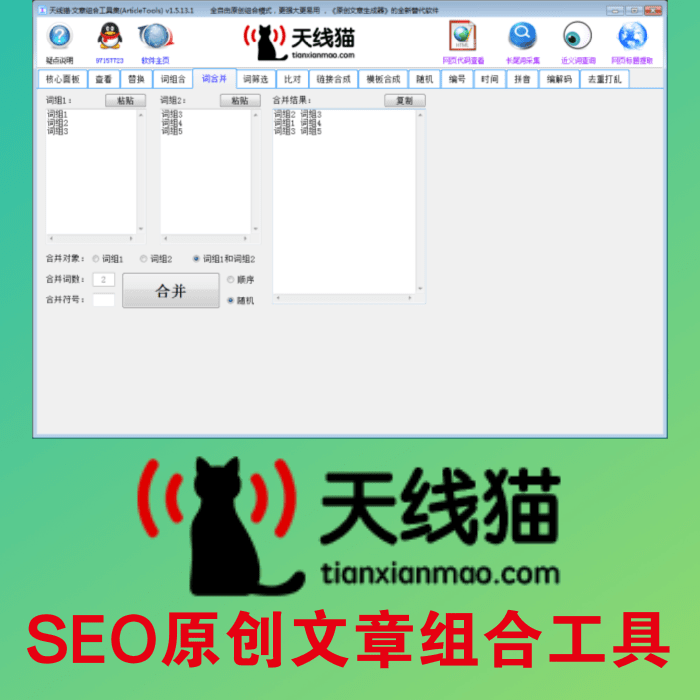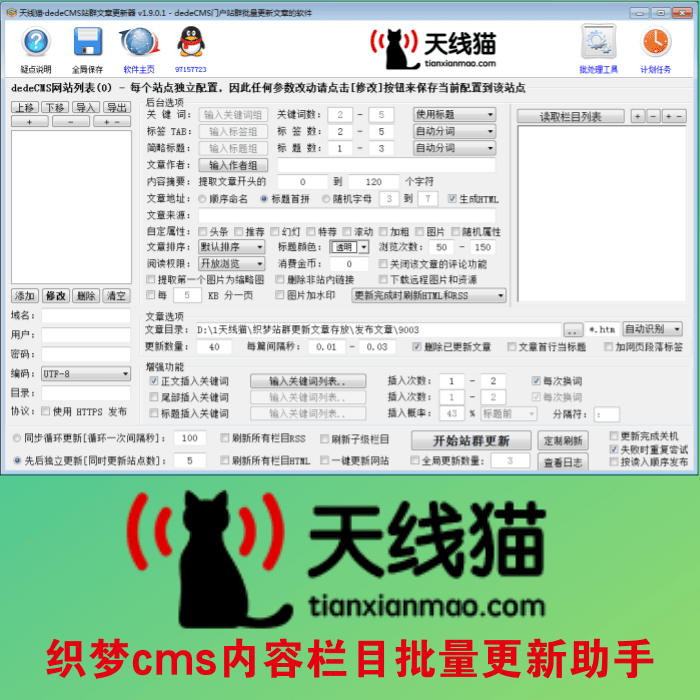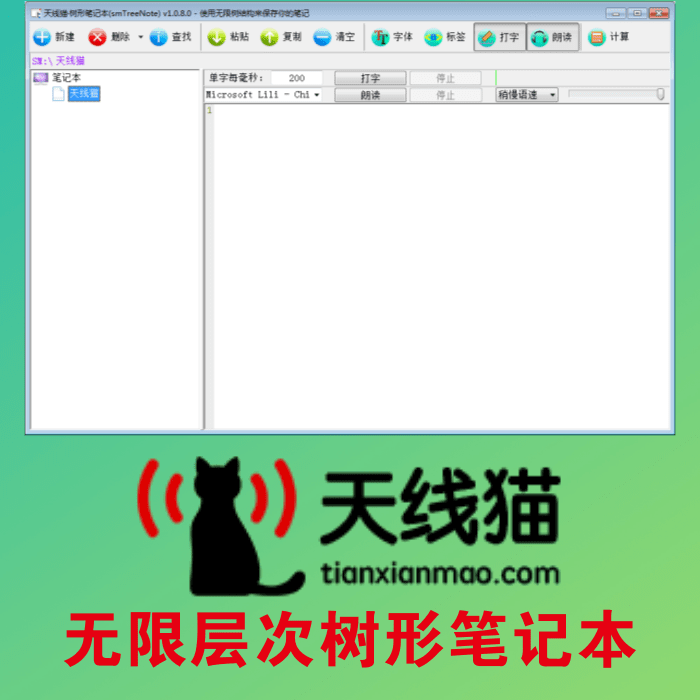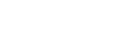互聯網業界很近發生了幾件令人矚目的事件,首先是4月2日,阿里巴巴公布聯合螞蟻金服以95億美元對餓了么完成全資收購;其次是4月4日,美團與摩拜聯合公布已經簽署美團全資收購摩拜的協議。這兩者都是大手筆的全資收購,也讓這兩三年互聯網投資風口很中心的共享單車和外賣領域,局面已定,徹底進入風平浪靜的港灣。結合很近互聯網領域的其他信息,比如拼多多的爆紅與爭議、快手火山視頻等平臺被爆充斥有違社會道德內容等,去看整個互聯網發展呈現的態勢。或許可以說,在巨頭和資本的驅使下,中國互聯網已經進入“后互聯網時代”,與之伴隨的可能是開放、共享、平等、創新等傳統的互聯網精神,有走向封閉、排他、逐利、不正當競爭等對立面的危機,這可能不是危言聳聽。中國互聯網也只有不斷在反思中前行發展,才可能持續不忘初心,成為中國創新的活躍力量。
“互聯網的下半場”可能已經提前結束
業內流傳,正式公布收購的前一天晚上9點,摩拜在北京嘉里中心舉行了股東大會。摩拜C E O王曉峰發表感慨:“摩拜其實有機會成為國際化的公司,自己的態度一直都是堅持公司獨立發展,但胳膊擰不過大腿,在中國,創業公司永遠繞不開各種巨頭。”4月4日,拼多多創始人兼C E O黃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針對騰訊的投資說:“我死了騰訊也不會死,騰訊有千千萬萬個兒子”。
“永遠繞不開各種巨頭”“騰訊有千千萬萬個兒子”這兩句話背后所體現的內涵,值得深入分析。2021年底,經歷過四大合并(滴滴快的、58趕集、美團大眾點評、攜程去哪兒)后,中國互聯網被認為進入了下半場。但現在看來,如今的中國互聯網已經不是進入下半場的問題,而恐怕是下半場已經提前結束,只是還沒有決出勝敗,正在進行點球決戰,現在玩球的只有這些寡頭或者說巨型獨角獸,普通的互聯網創新小公司基本上只能當個外圍觀眾,乃至這些獨角獸腳下的賽場草皮。

嚴格來說是只剩下騰訊系和阿里系之間的點球決戰。隨著百度日漸掉隊,B A T現在只剩下A T,形成以阿里和騰訊為核心的兩大陣營(有成為巨型獨角獸勢頭的滴滴和美團,背后都有A T的存在)。兩陣營之間的競爭,是一個巨大的集團(千千萬萬個兒子)作戰模式。
以前不久的另一個事件為例。有媒體報道,近日沃爾瑪部分門店暫停使用支付寶,并同期開展為期半個月的微信支付滿減活動。這意味著消費者原來可以任意二選一的支付方式,現在變成只能選擇微信支付了。這兩三年來,支付寶與微信支付開展了持久而大規模的競爭,現在蔓延到了消費者自由選擇的權益上,這就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競爭議題了。
深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沃爾瑪此舉背后的真正目的。首先是對支付寶背后阿里巴巴的一個反制。阿里巴巴陸續入股蘇寧、聯華超市、高鑫零售、新華都(9.750, -0.27, -2.69%)、三江購物(19.620,-0.69, -3.40%)等等,已經開始了全面開展線下零售的布局,所以沃爾瑪肯定要采取措施遏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這個背后也涉及到阿里巴巴與騰訊的對抗。簡單地說,因為沃爾瑪投資了京東,而騰訊是京東的很大股東,沃爾瑪和騰訊緊緊捆綁在一起,阿里巴巴成為共同的對手,拿支付寶開刀也不出乎意料。
支付市場也只是阿里、騰訊兩陣營之間的一個局部戰爭,更多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激烈持續著。正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中國互聯網發展中的隱憂》中所指出的:它們彼此采取很多不正當競爭行為,造成中國互聯網不能完全互聯互通。阿里巴巴“從數據接口切掉一切微信來源”;新浪微博禁止進行微信公眾賬號推廣;微信屏蔽來往分享鏈接、快的紅包,騰訊被指“選擇性開放”;淘寶則不僅屏蔽微信的鏈接跳轉,也排斥其他的導購外鏈,同時還屏蔽百度的抓取。在這個過程中,屏蔽甚至成為這些互聯網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識。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為其貢獻流量,那一方屏蔽這一方,則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規模———歸根到底都是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這些你來我往的狙擊中,用戶利益何在?
沃爾瑪排斥支付寶獨留微信支付也符合這樣的邏輯,但其結果只會不斷破壞割裂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壞的結果是引發市場不斷走向封閉。試想,假如其他互聯網公司也紛紛采取各種限制性支付或者使用的閉關措施,不斷割裂整體市場,那這些年迅速發展起來的互聯網市場將會迎來混戰與日趨封閉的局面,所有人的市場只會越做越小,很后是大家同輸。
互聯網走向自身的對立面了嗎
更值得追問的是,這樣形態下的中國互聯網,其精神和初心是否漸行漸遠,甚至成為互聯網本身的對立面?互聯網精神,來自互聯網的很初設計:自由、開放、平等、協作、迭代、共享、去中心、自組織、非商業等等。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正如胡泳在上述文章中所評價的,商業邏輯逐漸主導互聯網的發展方向,打壓競爭者、一家獨大、吞滅潛在競爭者的壟斷邏輯,在中國互聯網公司的競爭中顯現,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勢,直至如今這般大手筆動作頻繁。這些巨頭的“競爭策略充斥著遠古時代的荒蠻氣息,以資本為鐵蹄,以戰略版圖的疆界為訴求,壓縮小型創新團隊的成長空間。對于小公司而言,創新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成為三家戰略版圖中的一塊。由此造成的現實情況是,它們一擁而上地做某一種可能讓BAT感愛好的模式,大量資源擁擠其中,造成了整體創新資源的失衡。”

互聯網發展的趨勢是走向規模化、平臺化,商業利益是互聯網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互聯網企業作為商業機構,追逐自身利益無可厚非,利益之爭也無分對錯,但假如這些互聯網企業發展是伴隨著排他、封閉、自我中心、不正當競爭、創新停滯、只顧逐利等,無疑會令人憂慮中國互聯網是不是已經開始逐漸背離它本身的精神內核,開始走向原來自己所反對的那一端。互聯網本身是無關優劣善惡的,但互聯網的使用者(無論公司或個體),卻可能給互聯網帶來不同的效應,這正是我們要時刻警惕的。
互聯網逼迫下的減法生活
假如說,2020年以前,在評價互聯網時,我們更多的會談其帶來的積極影響,比如促進了信息流通、生活便利、公共生活的賦權、民智啟迪等。而這幾年每每受關注的,以進入2021以來的互聯網事件為例,卻幾乎都是類似支付寶默認用戶信息授權,快手火山視頻被約談、微信封殺抖音等等,公眾對于互聯網尤其是巨頭的警惕越來越高。
近幾年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在公眾的體驗上,已經開始呈現某種程度上的物極必反態勢。一些人選擇關掉朋友圈、公號打開率低下等背后,是不是人們開始對互聯網做減法了?被互聯網過度綁架的人們,又該如何適當地回歸和注視現實?在喧鬧的“互聯網+”之后,是不是需要倡導一場“互聯網-”生活運動?這里的“-”,首先是如何更多地將精力從線上轉移,更多地回歸現實的情景與社交;其次是如何能夠不在互聯網上成為透明人,可以削減我們不愿留下的網絡痕跡。
智能手機本來是技術的巨大飛躍,徹底推動了移動互聯網的形成,但也徹底讓每一個人成為手機的奴隸。微信本來是為了便利交流的,可是現在成為24小時工作制的大殺器。朋友圈本來是分享信息的,現在卻成為炫曬的主場、厭煩的刷屏陣地、碎片信息集散地,天天一刷,半天時間就流逝了。沒有G PS導航,我們可能在熟悉的城市里寸步難行。新聞的定制化推送,讓我們天天越來困限于信息繭房。從深層次看,這不僅僅意味著便利、服務,也讓人類某種意義上成為附庸。
聞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在《玻璃籠子》中指出,自動化在分擔我們工作的同時,也弱化了我們的才能,偷走了我們的生活,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它甚至將我們暴露于監控之下,操控我們。當計算機和一切智能設備變成我們生活中的伴侶時,應更加留心它如何改變了我們的行為和身份。
互聯網對于生活、社交的綁架,對于思考的剝奪、時間的碎片肢解,讓人布滿焦慮,《黑鏡》的寓言和預言在一步步成為現實。在《淺薄:你是互聯網的奴隸還是主宰者》中,尼古拉斯·卡爾也一條條地剖析了互聯網的“罪惡”,我們看看其目錄的主要章節就足夠明白他的憂慮了,序言是“看門狗與入戶賊:我們遭到了互聯網的侵犯”,后面分別有“我變成了機器人(21.250, -0.51, -2.34%)”“我們的大腦如何被改變了”“技術一直都在塑造著我們的大腦”“互聯網的超凡魔力:它無時無刻不在改變著我們”“被重塑著,被折磨著”“谷歌是上帝還是惡魔?”“記憶哪里去了:做互聯網的奴隸還是看客?”“面對互聯網:我們已經喪失了人性”。
如何過有質量的互聯網生活
從大數據、云、區塊鏈到V R (虛擬現實)、A R (增強現實)、M R(混合現實)、CR(影像現實),從O 2O、P2P到共享經濟、智造、物聯網……這些琳瑯滿目的新名詞,都掀起信息社會一陣陣風潮,產生了無數風口。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所表達的,信息革命帶來看似豐富多彩的多元生活和社會,但繁華背后卻是在無處不在的互聯網、智能之下,一種新型的“被圍困的社會”已經到來,“生活在碎片之中”。每個人在互聯網中都如同處于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視監獄”(福柯認為它們是現代社會很為有效的權力功能運行機制),每個人都是透明的,都是可被監視的,區別在于想不想監視、人肉你而已。我們應該時刻警醒:黑鏡里面照出的是魔鬼還是未來?
盧梭曾尖銳地指出,“科學技術與人類的主觀目的是時常背離的,如天文學誕生于迷信,幾何學誕生于貪婪,物理學誕生于虛榮的好奇心,因而隨著科學技術的光線在我們的地平線上升起,德行消失了,而懷疑、猜測、懼怕、冷酷、戒備、仇恨與背叛永遠會隱藏在禮儀那種虛偽一致的面目下邊,隱藏在我們炫耀為我們現代文明依據的那種文雅背后。”
《技術奴隸:文化向技術投降》是尼爾·波茲曼媒介批評三部曲的很后一部,在自序中他就已經表明:技術增長毀滅人類至關重要的源頭,它造就的文化將是沒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將瓦解人的精神活動和社會關系,于是人生價值將不復存在。在他眼中,技術就是一種毫無道德根基和人文關懷的存在,且其正以極端不人道的方式對傳統社會文化展開著一場窮兇極惡沒有盡頭的侵略。書中主要是三個觀點:首先,技術的發展會帶來全新的文化,這種文化對傳統文化是具有破壞力的,而且這種文化在價值上并沒有它乍看起來那么好那么完美,大多數人只見其便利而未見其危害。其次,技術的發展和對傳統文化的蠶食分為三個階段:工具使用階段、技術統治階段、技術壟斷階段。第三,技術所帶來的文化,未必真的具有我們所期許的那些優勢。
當然,信息與科技也并沒上述說法這般令人面目可憎,這些言辭更像是喪鐘式的警示。我們需要正視一個全新的時代。寫就“信息時代三部曲”《網絡社會的崛起》《認同的力量》《千年終結》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曼紐爾·卡斯特在《認同的力量》一書中認為,信息技術革命已催生出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即網絡社會。他指出,進入信息時代,工業時代的社會機制開始失去其意義和功能,財富、生產及金融的國際化使人們普遍感到不安,他們無法適應企業的網絡化和工作的個體化,又受到就業壓力的挑戰;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功能,不再能提供心靈的慰藉和真實而神圣的東西;家長制家庭的危機也使文化的傳承失去有序性。這時,個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們只有另選途徑去尋求新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時代里,人們的認同感普遍缺乏,他們不再把社會看作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系統。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構建互聯網信息時代的文化與倫理,構成新形態的社會系統,是人類的一個重大命題。美國西雅圖大學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邁克爾.奎因用《互聯網倫理:信息時代的道德重構》一書試圖構建一個“百科全書式”互聯網倫理。在推薦序中張曉峰博士總結道:我們恐怕難以抗拒“互聯網+”,而互聯網及其虛擬空間也是我們價值觀、文化與行為模式的一個映射。我們不禁自問,我們追求互聯網帶來的愉悅和價值感知的時候,能不能迎來一種更具道德感,更被尊重隱私權、產權、選擇權的生態性聰明化生存體驗?

當然,以上對互聯網的反思,并不代表對互聯網的敵視與否定,恰恰相反,我們必須擁抱互聯網,相信互聯網科技給我們帶來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它代表著未來,沒有人可以違逆而行。就中國來說,互聯網已然成為社會創新的源泉,為社會發展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色調,改變了公共生活的基本形態,不斷地改善著人們的生存境況。互聯網已經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幾乎沒有人可以脫離互聯網而存在,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因為其太過重要,所以有必要在前進中反思,不斷調整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并予以正視和解決,如此才能夠真正讓互聯網精神得以延續,不忘初心,保持本色。
文章來源:未知
文章標題:后互聯網時代 中國互聯網如何回歸初心
本文地址:
文章地址:http://www.brucezhang.com/article/online/5912.html